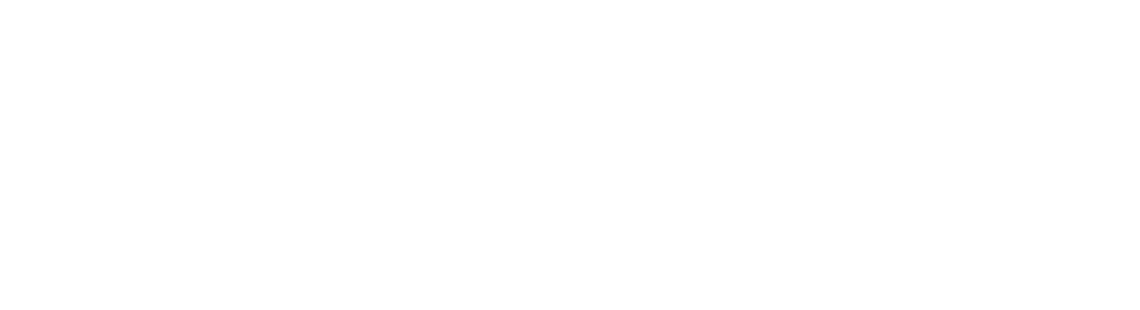作者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顧昕
來源 | 搜狐健康
摘要:在大多數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發展從社會醫療保險的設立起步。社會醫療保險是一種多元付費者體系,其內在固有的缺陷是碎片化,既有欠公平,也有損效率。去碎片化的途徑有兩條:一是通過政府強化給付結構的管制,為所有參保者提供一個平等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二是推動從社會醫療保險向全民公費醫療(即單一付費者體系)的轉型。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走上了第一條道路,也有不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了第二條道路。可是,無論是原生的還是后來引入的,全民公費醫療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和治理能力孱弱而無法滿足民眾對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的需求。發展中國家醫保的去碎片化,依然任重道遠。
關鍵詞:醫療保障;去碎片化;社會醫療保險;全民公費醫療;全民健康保險
建設一個覆蓋全民、運轉良好的醫療保障體系,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在當今中國,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城鎮居民醫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為支柱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并且自2011年起就實現了全民覆蓋(簡稱“全民醫保”)。
全民醫保的實現固然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由于在組織和制度上存在著碎片化問題,中國醫保體系呈現出制度失調和運轉不良的狀態。醫保碎片化既有失公平,也有損效率。許多老大難問題,遲遲難以解決。應對碎片化的措施,既缺乏縱向的一致性,也缺乏橫向的協調性,導致碎片化問題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愈加深重。零零碎碎的制度微調已經無濟于事。中國醫保體系亟待從碎片化到一體化的系統性改革。本文將從國際比較的視角,對社會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和全民公費醫療進行制度與績效的比較,為中國醫保的去碎片化改革提供國際借鏡。
醫療保障體系的發展與改革,屬于醫療需求側的制度建設。在世界各國,醫療保障體系有兩大主流的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Social Health Insurance, SHI)和全民公費醫療(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全民公費醫療和社會醫療保險之間,還有一種醫療保障體系,通稱為全民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健康保險的制度結構,實際上大同小異,僅在籌資機制小有差別,即前者的籌資基于一般稅收(general revenue),而后者的籌資基于醫保繳費。面向個人征收的法定醫保繳費,其實也可被理解為一種專項稅收,因此全民健康保險與全民公費醫療都被視為以稅收為基礎的醫保體系,全民健康保險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準全民公費醫療”。
具體而言,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的某些國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醫保籌資的主要來源實際上是一定比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因此,從籌資角度來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與英國的唯一差別,在于前兩個國家的醫保籌資基于事先確定下來的特定稅收,而后一個國家的醫保籌資基于年度一般公共預算。在給付層面,全民健康保險和全民公費醫療沒有什么制度上的差別,民眾看病治病時有一定的自付,但自付比一般都很低。把全民健康保險視為準全民公費醫療,這種做法并不脫離國際慣例。事實上,在國際文獻中,全民公費醫療(NHS)和全民健康保險(NHI)也常被視為同一種醫療保險體制。
在國際文獻中,社會醫療保險一般被稱為“德國模式”,其籌資來自參保者及其雇主的聯合繳費,其特點是醫保機構眾多,屬于“多元付費者體系”(multiple payers system)的一種。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健康保險的共同特征,是在一個特定區域(國家或地區)只有一家醫保機構為參保者提供服務,因此被稱為“單一付費者體系”(single payer system)。全民公費醫療由英國首創,一般被稱為“英國模式”;而全民健康保險模式由加拿大首創,因此通稱為“加拿大模式”。加拿大模式的醫保體系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實行,包括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臺灣,在臺灣的中文文獻中,稱之為“全民健保”。
除了少數國家,如美國、瑞士、南非、智利等,其醫保體系以私立醫療保險或私立健康保險為主之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在社會醫療保險、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健康保險之間進行選擇,以作為其醫療保障制度的主干。讓我們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兩個板塊,分別考察醫療保障體系的制度選擇。
一、社會醫療保險還是全民公費醫療?發達國家的制度選擇
作為發達國家的樣本,我們選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34個成員國為代表進行考察。以私立健康保險為主導建立醫保體系的OECD國家有兩個半,即瑞士和美國,以及智利。其中,瑞士通過頒布強制性全民參保的法令,自1996年起實現了全民醫保,而全民醫保的目標在美國至今也沒有達成,致力于實現這一目標的奧巴馬醫改實施艱難,而且在特朗普執政后有遭到徹底廢除之虞。
除了美國之外,所有OECD成員國都實現了全民醫保的目標。這其中,瑞士和智利較為特殊。瑞士的全民醫保體系以私立健康保險為主干;而智利醫保體系具有混合性,既有私立健康保險,也有社會醫療保險,一部分人群享有公費醫療或公共健康保險。
除瑞士和智利以外,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導建立全民醫保體系的國家有15個,以全民公費醫療為主導的國家有12個,另有4個國家的醫保體系以全民健康保險(即準全民公費醫療)為主導(參見表1)。如果我們把全民健康保險視為準全民公費醫療,那么可以說,社會醫療保險與全民公費醫療的制度競爭,從國家數量上來看,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但后者稍占上風(即15對16)。
從歷時態的視角來看,社會醫療保險的建立早于全民公費醫療或全民健康保險,或者說后兩者基本上都是在社會醫療保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早在1883年,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德意志帝國建立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隨后這一制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引入了其他國家。無論是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還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醫療保險都首先在正式就業部門推出,之后其覆蓋面再逐漸拓展到其他人群。到二十世紀末,在全世界,有27個國家通過社會醫療保險實現了全民醫保,而這些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險從部分覆蓋到全民覆蓋所經歷的時間大有不同。有些國家(如韓國)進一步將社會醫療保險整合為全民健康保險,而另外一些國家(尤其是在如德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等西歐國家)則始終維持著社會醫療保險為主的醫保體系。
全民公費醫療1948年正式在英國建立起來,成為社會醫療保險之外的一種替代性制度選擇。在16個建立全民公費醫療或準全民公費醫療的OECD國家中,只有英國和新西蘭在醫保體系建設的初始階段(即1940年代)就選擇了全民公費醫療,而其他14個國家是在1960-70年代、1980年代和2000-10年代這三個時期才從社會醫療保險轉型為全民公費醫療或準全民公費醫療。醫保轉型發生的緣由,在不同的國家不盡相同,但過程和結局大同小異。大體來說,如下三點是共同的。
其一是意識形態因素:在最早實現全民公費醫療的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影響力強大,而在英國主導全民公費醫療的工黨在意識形態上長期受社會民主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在那些全民公費醫療的后來者,尤其是南歐國家如有動力、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主要是左翼政黨執政期間推動了從社會醫療保險到全民公費醫療的轉型。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在福利體制中的體現,就是非商品化程度較高,即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福利成為一種普惠性的社會權利,人人享有,與就業狀況或勞動力市場的參與脫鉤。
其二是制度的整合性:無論是全民公費醫療還是全民健康保險,其特征之一是高度整合性,籌資的游戲規則適用于所有人,而醫療保險的給付結構也是整齊劃一的,這是單一付費者體系內在固有的特征。社會醫療保險則不同,由于是多元付費者體系,那么無論是籌資規則還是給付結構,不同的醫保機構都有可能不同,這就導致不同的參保者在醫療保險上的付出和收益大不相同,從而導致醫保體系呈現碎片化。
面對碎片化的挑戰,有兩種應對之策。一種是對社會醫療保險進行制度調整,即由政府針對繳費和給付設定統一的游戲規則,讓參保者至少就最低的醫療保障而言,繳費水平一致,給付結構劃一。在此基礎上,多元的醫保機構可以設立附加的規則,為醫療保障需求不同的參保者人群設定額外的繳費和給付規則。這種改革路徑,在學術上被稱為“有管理的競爭”,既能促進社會醫療保險的整合性,又能維持醫保機構的多樣性,從而在醫療保障體系中維持一定的競爭,促使醫保機構改善其服務。另一種是推進醫保體系從社會醫療保險向準全民公費醫療甚至全民公費醫療轉型,從而實現從多元付費者體系向單一付費者體系的轉型,既實現了去碎片化,也實現了普惠化。在OECD成員國當中,堅持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干建立醫保體系的15個國家,選擇了第一種去碎片化路徑,而其他國家則選擇了第二種路徑。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墨西哥處于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過渡階段。在OECD成員國中,在社會保障體制上與中國最具有可比性的國家莫過于墨西哥。在2004年以前,墨西哥的舊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在就業的基礎之上,而其醫療保障體系以社會醫療保險為制度主干。但是,以就業為基礎的社會醫療保險難免碎片化,不僅未能實現全民醫保,而且還對醫保體系的公平和效率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進入二十一世紀,墨西哥政府致力于將民眾的健康納入到社會保護(福利國家的另一種性說法)體系之中。2004年,面向未納入社會醫療保險的民眾,墨西哥政府設立了大眾健康保險,籌資來源包括參保家庭定額年繳費和政府補貼(由聯邦和州政府兩級分擔),人口最貧困的20%家庭免繳費。2012年,墨西哥于推進進一步轉型,實現了全民健康保險。這一過程意味著醫療保障在墨西哥從就業福利轉型為公民權利,從而成為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體系的內在組成部分。在新體系中,所有民眾均能根據需要接受基本的醫療服務,而費用主要來自于兩級政府的財政預算。民眾依然需要繳費,而繳費規則不再如以往的社會醫療保險那樣基于工資稅,而是基于特定的醫保繳費,但民眾繳費在醫保籌資上已經無足輕重。換言之,類似于中國城鎮職工醫保的舊醫保制度在墨西哥逐漸消亡,醫保體系與就業狀況徹底脫鉤了。
其三是制度變革的路徑依賴性:從社會醫療保險向全民公費醫療的轉型一旦推動并初步成型,就幾乎不大可能逆轉,最終只能沿著新制度框架不斷演變并加以完善。這一轉型意味著醫保成為全民共享的一種普惠性社會福利,而普惠性福利的削減一般都會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彈,遑論全盤取消。即便出現經濟波動甚至面臨經濟危機導致政府采取財政緊縮措施,例如在希臘,全民公費醫療制度都能屹立不倒,盡管其保障水平有一定的下降。
二、全民公費醫療與社會醫療保險的績效比較
對于全民公費醫療和社會醫療保險的優劣,國際學界曾開展過一定的比較研究,基本結論是,如果制度設計合理且治理水平較高,兩者的績效不分上下。當然,如果制度有缺陷,且治理水平有高低,那么兩種制度本身內在固有的缺陷會放大。至于兩者的利弊比較,可以取得共識的結論有四。
其一,如果一般稅收呈現累進性的話,全民公費醫療也就具有累進性,從而顯示出更高的籌資公平性,而基于工資繳費的社會醫療保險多呈現籌資累退性。當然,這兩者的對比程度取決于全民公費醫療中稅收籌資和社會醫療保險中保費籌資的制度細節,尤其是后者。
例如,在德國和荷蘭,社會醫療保險繳費基數是就業者的薪酬,但并非全部薪酬都作為繳費基數,而是設有最高額度限制;而且,高薪人士還有權離開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去購買私立醫療保險。這就意味著高薪人士參加社會醫療保險的繳費水平與其收入水平之比,平均而言,要高于低薪人士,這就導致社會醫療保險的籌資機制呈現累退性。但在法國,所有就業者都必須參加社會醫療保險,且不對繳費基數設定最高工資限制。這樣,法國社會醫療保險的累退性程度要弱于德國和荷蘭。在中國,城鎮職工醫保的繳費基數僅為基本工資而不是全部薪酬,這意味著低收入工薪階層的醫保繳費相對較多,此外還有不少雇主(繳費單位)故意壓低高薪雇員的社保繳費基數以減輕自己的社保繳費負擔,這就使得中國城鎮職工醫保的籌資呈現出一定的累退性。
其二,全民公費醫療的財務可靠性不及社會醫療保險。全民公費醫療的籌資基于一般稅收,這樣醫療籌資的水平取決于年度政府財政預算安排,而預算編制受到諸多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的制約,在很多情況下透明度和穩定性相對較弱,醫療開支被擠占的情形并不罕見。
在醫療費用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全民公費醫療國家醫保支出的穩定性普遍不足。簡單說,由于全民公費醫療的運作在財務室完全依賴于公共財政支出,那么政府投入水平的高低對于其運行績效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政府投入不足,那么全民公費醫療便有可能既沒有效率,也不能帶來公平。
相比而言,全民健康保險的籌資基于專項稅收,其籌資透明性、穩定性和制度化程度高于基于一般稅收的全民公費醫療。這也是全民健康保險作為一種準全民公費醫療制度在全民公費醫療制度成熟之后有所創新之處,而這一制度1984年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創立之后,也為韓國、墨西哥等國所采納,而智利則是在2004-2005年間在其既有的私立醫療保險、社會醫療保險、公費醫療體系之外,引入了全民健康保險的制度要素。
社會醫療保險的籌資基于專項繳費(亦可理解為“工資稅”),其籌資水平與薪酬收入增長掛鉤,且其籌資所得全部用于醫療保障,籌資水平與支出水平的關聯相對清晰。無論被視為征稅還是繳費,只要籌資與支出建立真正的聯系,都會使整個醫療保障體系更加透明,也更容易得到公眾的支持。
從OECD代表性國家衛生總費用(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THE)占其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等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情況下,全民公費醫療國家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普遍低于社會醫療保險國家。全民健保國家只有四個,而且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加拿大在衛生總費用上的支出表現強于其他可比的全民公費醫療國家。
就業正式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影響,在今天更是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關切。在當今世界,非全職工作、多職工作、非正式就業早已成為工作與就業的新常態,這一點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也是如此,而社會醫療保險乃至更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如何在非正式經濟的基礎上鞏固與發展,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管理挑戰。只有少數國家成功應對了這一挑戰。荷蘭將兼職工作與多職工作納入到福利國家的種種制度安排之中,被稱為就業促進和福利改革領域中的“荷蘭奇跡”。
其三,社會醫療保險的良好運轉高度依賴于正式的就業體系,而雇員與雇主的聯合繳費不僅要負擔雇員本身的醫療保障,還且還要負擔雇員家屬以及社會弱勢人群的醫療保障。社會醫療保險會給就業體系或勞動力市場帶來沉重的壓力,因此比較適合于正式就業占據主導且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例如德國、法國、荷蘭和日本等。對于工業化程度偏低或非正式經濟部門比重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來說,基于稅收的全民公費醫療或全民健康保險更有可能運行良好。這也是相當一部分OECD國家將社會醫療保險為主的醫療保障體系轉型為全民公費醫療或全民健康保險的部分原因所在。
其四,正如前文所論及的,作為多元付費者體系,社會醫療保險容易出現碎片化的問題,即對于民眾而言,繳費規則不一,給付結構各異。碎片化不僅會有損于公平,而且還會引發制度運行不協調的問題,效率不彰。民眾還會因所參加的醫保有所不同而出現身份不同的現象,當他們身份轉換甚至工作與生活的地點變化時,都需要采取行動轉換身份才能讓醫保關系延續下來。這些問題在全民公費醫療和全民健康保險體系中根本不會存在。
三、發展中國家的醫療保險:在社會保險、健康保險和公費醫療之間掙扎
究竟是公費醫療好,還是社會保險好?理論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世界各國的實踐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實際上是各有各的利弊,優劣難分。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政府財政能力偏低,導致衛生總費用水平較低以及公共部門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比較低,一旦實施全民公費醫療,往往會導致公共部門醫療服務供給的不足,致使全民公費醫療徒有虛名。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正式就業相對孱弱,采取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也會導致制度設計缺失很多、治理水平低下。無論是公費醫療還是社會保險,其本身的內在缺陷往往會放大,導致醫保體系的整體運作績效不彰。
發展中國家醫保體系的發展情況,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醫保體系極端不發達,無論是公共醫療保障,還是私立醫療保險,都不發達,只有少數特權人群(即公務員和公共部門雇員)享有公費醫療或醫療保險。
第二類發展中國家通過建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逐漸完善醫保體系。同發達國家有類似之處,多數發展中國家是從社會醫療保險起步,首先為正式就業部門中的就業者及其家屬提供醫療保險,然后再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引入公共健康保險的制度要素,將醫保覆蓋面拓展到其他人群,例如自雇者或非正式就業者、非就業人群、農村居民等。在此過程中,社會醫療保險+公共健康保險的體系往往呈現出碎片化之勢,即不同的人群由不同的保險制度所覆蓋,最后導致籌資規則不一,給付結構有別。碎片化的醫保體系不僅公平缺失,而且效率不彰。而且,面對非正式就業人群,以薪酬為籌資基礎的社會醫療保險實施起來非常困難,而以自愿性繳費為籌資基礎的公共健康保險也面臨著嚴重的逆向選擇問題,無法實現廣覆蓋,更談不上全覆蓋。
第三類發展中國家,一開始就建立起全民公費醫療,但由于政府財政投入不足,全民公費醫療體系無法為民眾帶來公平、適當的醫療保障。面對低水平全民公費醫療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政府不斷地采取打補丁的方式加以應對,要么不斷引入一些面向就業者或高收入人群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要么由政府補貼設立一些公立健康保險項目,試圖達成一種高水平的全民醫保格局,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整個醫保體系和醫療體系呈現出高度碎片化。
這類國家,一部分是轉型國家,從社會主義的全民公費醫療轉型為公費醫療、社會保險、健康保險混雜的醫保體系,俄羅斯就是這類國家的典例。蘇聯崩潰之后,俄羅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即在葉利欽當政初期,國家財政緊張,社會安全網被撕裂,全民公費醫療制度入不敷出。百姓看病治病,雖然號稱免費,但自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面對這一情況,俄羅斯政府引入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由于不同的人群參加的醫療保險不一樣,繳費水平不一,因此呈現一定的碎片化。為了應對這一局面,俄羅斯政府在醫保給付結構的去碎片化上下了一定的功夫,即定義了一整套“基本醫療服務包”,對所有國民基本上免費提供。
另一部分是一些英聯邦國家,借鑒英國模式建立了全民公費醫療,印度就是這類國家的典例。早在1950年,印度就建立了全民公費醫療,民眾可以在公立醫院享受到基本上免費的醫療服務。但由于政府投入水平太低,公立醫院無法滿足民眾對公費醫療的需求。印度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且公共部門支出的比重一直很低,私立醫療保險在印度也很不發達,民眾自付的占比很高。為了讓低收入民眾能夠享有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印度政府一方面維持既有的全民公費醫療體系,另一方面又推出了許多政府資助的自愿性醫療保險項目。2008年,一個新的全國性公共健康保險計劃(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ana,RSBY)設立,專門為貧困家庭提供住院保險。印度政府對于提升其既有的全民公費醫療缺乏系統性和一致性的措施,而只是采取打補丁的方式進行小修小補,最終導致整個醫保體系的碎片化。
第四類發展中國家屬于少數,由于歷史原因,私立醫療保險較為發達,但其覆蓋面集中在某些經濟發達地區中的中高收入人群,無法實現全民醫保。對此,政府采取積極干預措施,建立全民公費醫療或全民健康保險。金磚國家中的南非和巴西就是這類國家的典例;而上文提及的OECD新成員國智利,也是這類國家的典例。
南非、巴西與智利醫保體系的特點在于:首先,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并不低,金磚國家的南非和巴西還高于OECD成員國智利;其次,衛生總費用中公共支出的占比都很低,均低于50%,而南非和巴西在這一指標上還略強于智利,這說明這三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在醫保體系的建設上發揮主導作用;再次,私立醫療保險均較為發達(參見表1和表2)。
在很大程度上,南非和巴西(以及智利)的醫保體系正走向美國模式,即形成私立醫療保險占大頭,并與社會醫療保險、公共健康保險、公費醫療服務混雜性的格局。
南非的醫保體系繼承了種族隔離時期留下的“荷蘭式遺產”,呈現社會醫療保險和私立醫療保險混雜的格局,其主要受益者是收入水平較高的白人、公務員以及少數正在興起的中產階層黑人),不僅高度不平等,而且效率也不彰。非洲人國民大會黨自1994年執政以來,引入了全民公費醫療制度,以應對中低收入人群的醫保需求。新興的公共醫療保障體系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但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依然無法滿足廣大民眾的公費醫療服務的需求。
巴西在1988年以載入憲法的莊重形式建立了統一醫療體系(Sistema único de Saúde, SUS),并將健康作為一種公民權利和國家為民眾提供健康服務的義務入憲。SUS是一種準全民公費醫療體系,其籌資來源于多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和特定的醫保繳費,其給付結構劃一。盡管巴西所有民眾都能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公費醫療,但保障水平還有限,私立醫療保險依然舉足輕重。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的一項研究指出,巴西醫保體系在去碎片化和普惠化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政府能否對公費醫療體系給予穩定的、充足的投入以及如何管制醫療領域的公私關系,是最大的挑戰。
四、結語:社會醫療保險的碎片化
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醫療保障體系的發展大多從社會醫療保險的設立起步。社會醫療保險是一種多元付費者體系,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醫保機構參保,繳費和給付的游戲規則極有可能不盡相同,從而導致個體的醫保身份化以及整個醫保體系的碎片化,既有失公平,也有損效率。此外,社會醫療保險在籌資上以工資稅為基礎,本身存在著累退性的不公平問題,而且對正式就業體系或正式勞動力市場參與的依賴性較高。
相對來說,全民公費醫療的籌資依賴于一般稅收,如果整個稅收體系具有累進性,那么醫保體系也就具有累進性,公平程度較高。在全民公費醫療體系中,給付結構對所有人都一樣,沒有碎片化的問題,而且醫保與民眾的勞動力市場參與脫離了關系。全民健康保險是一種準全民公費醫療制度,其特點是籌資依賴于特定稅收。全民健康保險的籌資水平取決于特定稅收本身的情況,比較穩定,而全民公費醫療需要與其他社會經濟發展項目競爭公共預算資金,因此其籌資水平不大穩定。
面對社會醫療保險內在固有的碎片化傾向,不少發達國家通過強化政府在醫保給付規則上的管制,使得所有參保者都享有平等的基本醫療保障服務包。西歐國家、日本和以色列都在社會醫療保險為主干的制度框架中實現了去碎片化,同時也保留了多元付費者體系中醫保機構之間必要的競爭。轉型國家中的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也走上了這一道路;相對來說,俄羅斯醫保體系的去碎片化進展稍慢一些。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發達國家以推動社會醫療保險向全民公費醫療或準全民公費醫療的轉型,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醫保碎片化的問題。有些發展中國家要么一開始就實施全民公費醫療,要么也走上了從醫療保險向公費醫療的轉型之路,但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以及其他制度設計和治理能力上的缺陷,全民公費醫療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全民對公費醫療的需求。在醫保體系的去碎片化和普惠化上,發展中國家還任重道遠。
(本文轉載自顧昕教授公眾號,原文題目《社會醫療保險與全民公費醫療孰優孰劣? ──醫療保障制度的國際比較》,參考文獻省略)


 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西三道街49號
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西三道街49號